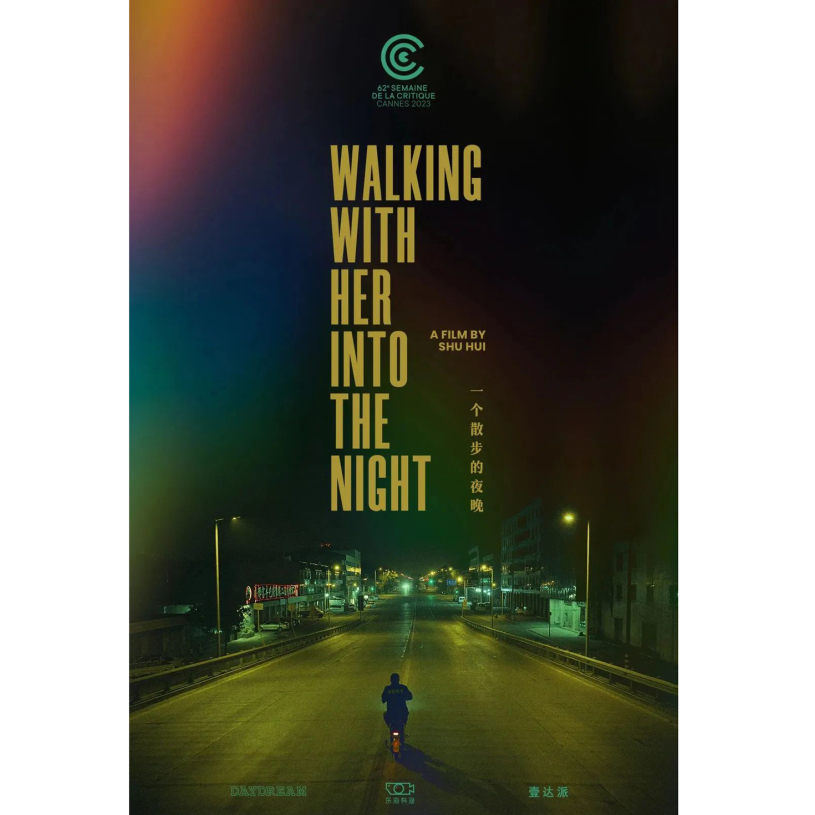当记忆中的街道变了模样,幼时熟悉的面店变成了酒吧,久违回到故乡的她成了“异乡人”,难以适应新的变化;而酒吧里的调酒师相信,回忆是不断叠加的,与其固守脑海里的美好,不如接受新的变化,让一切过往成为新的年轮。两个有着截然不同人生态度的人走近彼此,以物寄情,展开了一个有关归属与变化、留恋与释然的故事。


A FILM BY 何一非 STARRING 朱一龙 倪妮

子悠站在露台上。一个服务生拍了拍她的肩膀,递给她一张拍立得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老太太,背后面馆的招牌被挡了一半,只能看到面馆二字,仔细看的话,墙上还有门牌号。
白色T恤 PortsPURE 浅卡其色风衣 MaxMara 阔腿牛仔裤 Giambattista Valli 珍珠项链、戒指 均为Tasaki
子悠来到一家酒吧门前,暖黄色的光将小店照亮。她望着里面的满目琳琅,犹豫片刻,决定进去看看。

此时,酒吧老板程磊拿着几瓶汤力水,正在忙碌。
印花衬衫 Brioni 白色长裤 Ralph Lauren 腕表 Chopard
程磊:“我们还没开门 ,晚上八点正式开始 。” 子悠:“你这原来是个面馆吗?”

程磊面露一丝诧异。他打开一瓶苏打水,倒入盛着棕色的酒的杯中。 “不是面馆,好像是理发店吧,你有什么事儿吗?”
子悠匆匆扫了一眼周围,有些失落。她向门口走去,准备离开。

程磊从柜台里拎出一个彩色条幅,上面用卡通的字体写着“关门大吉”的字样。 “明天之后这就变成面馆了,还是一家连锁网红店。”


“以前每年春天,这家面馆都会把榆钱放在炝锅面里。小时候我考试考不好,我外婆都会带我来这家面馆吃面。外婆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国外。这么多年没有回来,这里变化好大。我还以为老字号的店能留下呢......”

“今天来喝酒的每个客人,都必须带走一样东西。带走之后,每次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想起这家店,就像你忘不掉那个面馆一样。”
一杯“春风”摆在子悠面前。几片榆钱碎撒在其中。
子悠喝了一小口,将酒杯递给了程磊,示意让他自己尝尝。程磊有些诧异,接过酒杯,抿了一小口。 两人四目相视,欣慰地笑着。

/朱一龙: 故事里的他/
采访时,朱一龙很多次聊到不想再重复自己。打开是一种勇气,松弛也是一种勇气,主动往前一步,让更多东西融进来的过程没那么悠闲自在,但这样一路走来,他身后已经有了很多角色。朱一龙并不打算回头。 撰文:闫夏
印花衬衫 Louis Vuitton 黑色夹克 Peter Wu 黑色长裤 Nanushka 腕表 Chopard
向上滑动阅览
一杯面条 在朱一龙看来,《春风》的片长只有十分钟左右,却是一个关于回忆和寻找,关于以前、现在和将来的故事。当倪妮饰演的子悠凭借记忆中的味道回到老地方,他出演的调酒师程磊首当其冲成为“干扰项”,闯入了子悠对旧时光的执念。女孩是来寻找儿时老面馆的,也最终从程磊这里得到了那份放了榆钱的面条。但和原剧本预设的不同,在《春风》成片里,榆钱面不在碗里,而是被盛在一只有斜眼睛的“丑杯子”里。这是演员们片场迸发的灵光。回想拍摄的过程,朱一龙仍然觉得这个点很有意思。如果说《春风》中的子悠站在从前和现在的交界,程磊则站在现在与将来的交界。这是他酒馆的最后一夜,丑杯子是客人们可以带走的念想,用来在未来怀念今夜。“我觉得它表面上和潜在里都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可解读性比寻常的容器更强一些”,朱一龙说。正如故事里的“味道”容纳着许多层复杂的感受,光影中的镜头所及也藏有明明暗暗的线索。很多时候,演员既是听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也是潜入故事去触发线索的人。片场监视器会将创作者的不同状态完全记录,屏幕中的朱一龙清瘦,专注而忙碌。不表演时,他会自己演练调酒动作,或是和倪妮与导演在吧台前讨论,薄薄的台本在他手中已经有点皱巴巴的。 他的故事 这次朱一龙和倪妮重聚,契机也是《消失的她》即将上映。朱一龙说,刚开始他会有一点点抗拒何非这个角色。看剧本时,他被何非吸引是因为他的复杂,抗拒亦然。“整个故事戏剧性很强,但是这个角色就很容易变得很‘抓马’。”《消失的她》的故事也是他的故事。塑造何非的第一重难度来自未知。相比脉络连贯的角色,何非的成长拼图是有遗失的。在拍摄过程中,朱一龙需要在很多次“闪回”中塑造角色,他永远诠释着何非的“现在”,所以对演员而言,人物的空白是不容存在的——他理应是最了解他的人。于是当开始准备角色,进入拍摄,朱一龙的创作就分成了两条线程:第一条是作为演员完成高爆发力的表演,第二条是像侧写者一样补全何非的碎片。“最主要还是捋这个人物,比较痛苦的过程是你得把他所有的心路历程合理化。你内心得知道他在各个阶段里面临过什么,然后去抓取他那个阶段的时候在想什么。镜头之外的这些部分是需要自己去把它补完、理顺的。”而最终在这条线上,朱一龙的侧写是有结果的。他提取出一句话来辅助他拆解何非的历史:“每个人都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但你可以选择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看似鸡汤,但当看过故事,就会了解何非的一切曲折和张力,挣扎和失衡,决定性的念头,都是在可选与不可选的矛盾间被激发。 对朱一龙来说,饰演何非的第二重难度是建立认同。从开机起,他就不断和监制陈思诚,崔睿、刘翔两位导演在讨论何非的“为什么”。毫无疑问,何非是一个和他完全不同的人,很多时候,朱一龙需要拼命告诉自己“何非在当下的选择是对的”并且为他的所有选择找到理由。所以在剧本的水面之下,朱一龙有一个自己版本的何非故事。在他的故事中,何非与妻子李木子的生活有了非常细致的进展,但那些存在于性格底色里的东西总会在十字路口冒出来。运气和捷径曾经为何非带来过选择权,然而也正是它们让他错失了平衡欲望与能力的机会。表面看,何非几乎已经得到一切,但事实上,他从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叙事。 采访是在电影上映前进行的,朱一龙在谈论处理角色的细节时犹豫过几次,他很想多说具体的部分,包括他甚至为何非设定了婚后职业和职场表现。“哎呀,这应该等电影上了之后说”,表达欲上来,又不能剧透时,他就总是语速很快地提醒自己一句,然后还是忍不住开聊了。何非与朱一龙的差别让这位男演员几乎难以理解他,但谈到与角色的关系,朱一龙却相信他们一定是“相同”的。塑造角色的过程,也是将演员看待世界的眼光、观察他人的视角、从生活中汲取的事物赋予人物的过程。 内紧外松 在倪妮眼中,片场的朱一龙大多数时候很安静。“龙哥”沉在状态里时,剧组的大家各自忙碌,也都不会去搅扰他。两位演员在表演和交流方式上都很合拍,这种契合也被带到《春风》片场。有趣的是,尽管拥有各自的故事,两位演员在采访中都提到自己最近几年进入了某种创作状态,大概是一种内紧外松的情境。其中的松弛一部分来自于设想和现实的差别。在朱一龙过往的体验中,每天在现场发生的事情和所处的环境都是变化的,头天晚上设计好的东西到了实地经常不能完全适配,这会给他带来一种落差感。“这样的次数经历得多了,我现在就更愿意让自己尽量把整个人物捋顺了,你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然后在面对每一场戏的时候,就尽量去感受现场,放松去感受就好。”而松弛的另一部分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朱一龙是在这两三年明显有这个改变的。“其实你预想得越好,表演的设计感就会越强。你的人物身上的设计感也会越强,你就很难还原他本身的样子。”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有一部分内核是收紧和节制的。我们总是好奇演员表演的高峰体验,想听朱一龙说说“演得很爽”的那些时刻。但他说,其实自己在拍戏的时候很难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因为在整个拍戏的过程中,他都是纠结的,是绷紧一根弦不断在调整细节的。在《消失的她》中,因为何非的复杂性,也因为要仔细掌握戏剧化和“抓马”之间的分界,朱一龙的拍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修正的过程。控制是一种精密的体验,站在最终呈现的角度,演员完全撒开了去享受表演的状态未必真的是好的。“你的第一自我永远在监控着你的第二自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朱一龙在谈论自己别的作品时,总会更着重去聊他和人物相遇的故事,成为他们的瞬间,还有对人物命运性格的体验。但说起《消失的她》,朱一龙说:“这个戏确实是要去‘表演’的,它不是一个完全走生活流和生活逻辑的作品。”它的很多场景是偏舞台化戏剧式的,这就要求他给出更夸张、戏剧性更强的表演状态,但这其实不是朱一龙习惯的创作方式。不过也是在这样的一次次不习惯中,朱一龙感受到了自己创作思路的变化。这或许也是另一重“松弛”吧。“我现在觉得,你不光要适应不同的角色,你还要适应不同的创作团队。这样在本质上,你的表演和你的人物才能发生变化。如果我一直坚持内心所谓的我认可的好表演,一味坚持的过程其实还是不断在重复自己的过程。”所以这几个月的体验是怎样的呢?他进入到首次合作的电影团队,虽然有些不熟悉,但试着尽量去吸收创作团队想要表现的东西。他相信自己,因为表演的记忆已经长在他身上,不用刻意去突出和坚持,那已经是他紧凑的一部分了。首先做出的改变是建立信任,信任团队和大家,然后一起做一个不一样的戏,一个不一样的人物。“你得不断去尝试,有这样不同的作品来找你,你才有机会去印证这个事情到底做得对不对”,朱一龙还在测试方法,看怎样能不在自己习惯的创作思维和表演方式里重复,但至少几件事是很确定的:他相信实践出真知,正如表演不能靠头一天晚上的想象,得把它演出来才知道试得对不对;他相信“不要抗拒”,“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只有你自己眼前这么多,有些东西看似不合理,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所以试着先去了解,然后去感受,感受完了我们再探讨合不合适,应不应该去做。别人说了什么,你就说不行,我不能这么演,这个过程我觉得已经在重复自己了。”所以,或许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在我们没去过的人海里,何非就是在这样生存着的…… 与人 朱一龙说,演员一辈子都在演人,“你不断在观察人,也在不断地去探讨人性”。塑造角色的过程,或许有时也是一种对演员自己的开解和陪伴。他说自己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去想死亡这件事,“什么是死亡,死亡之后人会去什么地方?小时候莫名地就会去想,所以我小时候总会莫名地感到伤感,因为未知,所以你会对它充满恐惧。”成年后,死亡则成为了大多数人在生理上完全懂得却不愿意去想的存在。“演完《人生大事》,虽然对死亡还是没想明白,但我就宁愿相信说,去世的人就变成天上的星星,在天上看着你。选择相信像这样童话般的故事,我觉得能让自己心里稍微豁然开朗一些。”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对人的观察与体会也是朱一龙坚持拍电影的原因。“因为拍电影之前,特别是偏现实主义题材的戏的时候,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去想你想把人的什么东西带入到这部电影当中,这可能电影才能办得到。”所以他在每一个新作品开始前,都会留出大量时间去故事发生的地方体验生活,感受环境,去建立与人或人性之间的连接。《河边的错误》是有浓郁时代感的故事,朱一龙的角色马哲又有特定的职业属性。带莫三妹参加完金鸡奖颁奖礼的第二天,朱一龙就来到江西东南的南丰县,开始了两个月的县城生活。在那里,他要把马哲的衣服慢慢穿成他的衣服,也要和八十九十年代的老刑警队长们交谈相处。“体验角色的过程,对于演员来说真的是一个帮助,能让你不断对人有好奇心。因为你会有机会通过每个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时代背景,接触到你原本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的人。”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在小城南丰的街道,你会看到一个有点生的脸孔。他打扮得并不入时,穿着旧旧的皮衣。当然,这就是下一个有关他的故事了。
/倪妮: 春风自然来/
在《春风》中,倪妮是对儿时记忆略带执着的子悠。子悠在春风中经历了寻找和释怀,而身为演员的倪妮也在不断体验与精进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与自己的“固执”共生的松弛。 撰文:闫夏
皮质连帽夹克、紧身长裤、高跟长靴 均为Alexandre Vauthier 造型耳环 Schiaparelli
向上滑动阅览
灵活的固执 倪妮总说,她是一个固执的人,接演一个角色一部作品时,需要被充分说服。而《消失的她》中的陈麦,对故事有关键性推动作用,同时有清晰的成长脉络和心理变化,有内心活动的递进,有自己的历史,她本身便形成了一个可推敲的过程。在倪妮非常在意的角色想象空间和逻辑上,陈麦说服了她。 《消失的她》是一部快节奏类型片,倪妮之前很少出演这样的故事,于是她提前去看了不少同类片子,想了解在这个题材中演员最终会呈现怎样的表演状态。“但有的时候准备是两面性的,你看的过多,想的过多,在现场越会有一种事与愿违的感觉,你想象当中的和实操总会有一些差别,一旦这种差别形成,就很容易会在表演上痛苦”,倪妮说。而在紧张紧凑的剧情之下,《消失的她》悄悄记录下的反而是倪妮在这一部分的松弛。在确保陈麦这个角色合理,逻辑通顺的基础上,倪妮有意为自己、对手演员和导演之间留出了灵活的、未经想象的余地。“监制和导演也会有他自己的创作想法,对手演员也会有他非常临时的表演状态,所以有时就不要做太过于充分的准备,给自己和临场发挥留出充分的空间。” 乐趣也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产生的。出演何非的朱一龙是倪妮这次的对手演员。在片场,倪妮和朱一龙聊戏的时候有很多。当故事发展到中后期,陈麦与何非的情绪交锋会越来越密集,在越发紧凑的事件和事件之间,演员给出的情绪变化充当着转折的粘合剂。剧本文字在这个时候既压缩了情绪的层次,又因为“扁平”给了情绪无限可能。倪妮和朱一龙探讨和研究的就是情绪变化的不同呈现。“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临场反应,喜欢在一场戏去尝试不一样表演状态的演员,所以我们一起拍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两个人在意识上是一样的”,倪妮说。 创作一定是严肃认真的,但在此基础上给自己留一点“玩心”,是另一种的尊重创作的方式。倪妮记得,自己的变化发生在出演《天盛长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她第一次演电视剧,“还是一个在技巧上比较笨拙的演员”,因为很想把事做好而压力很大。于是她陷入了一种强迫自己的状态,“每一场戏台词不管多少,我都要画正字准备二十遍,哪怕到凌晨三点。”后来,倪妮去请教对手演员陈坤,问他那么多台词每天要背到几点。陈坤说,他都是早上起来背的。陈坤告诉倪妮,演员做充分功课的想法和意识都是很好的,但他有时候会让自己不把一些东西记得太熟,要允许自己在现场有一个反应的空间,而不是当面前人讲台词时,自己脑子里已经在背课文般想后面要说什么了。就像在讲被剧透了凶手的悬疑故事,演员此时过于精准的反应,反而会变得模式化。从那以后,倪妮也开始尝试不同的方式。她开始更习惯记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逻辑,记住他们要发生的事情,让自己有更多机会真实地在场,去反应去感受。 练习 起初,倪妮也花了点时间去适应《消失的她》。“类型片的表演方式跟我之前认知到的会不太一样,类型片的成片是靠剪辑、音乐和演员表演配合起来形成的节奏。在现场,监制和导演会要求一到你,你必须要把情绪表现出来,或者要给出夸张的表演,但可能我自己的心理节奏并没有那么快,也会担心夸张的表演会假,所以其实刚开始是有点不太适应的。”但在几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她渐渐进入了这种她原本不熟悉的创作方式。很多部分也是在懵然无知或飞沙走石般的体验中完成的。比如她依然很不喜欢配音,依然觉得现场的空间感和对象感无法复制和替代,并且在配那场车里的戏时发现自己很难再回到当时的心理节奏,很难跟上自己拍摄时的语速;比如在一段行走的戏中,她需要在一条很短的路上表演出好几层情绪,“我本身走路快,迈的步子又大,在那种情况下你又需要跟摄影师配合,但表演就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你不能够什么都顺着自己的感受来,也不能够完全按照你最舒服的方式,所以演员要努力调整自己,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这就是倪妮,直白准确真实地表达自己所想,没有多余的公式化铺垫,没有无悲无喜的姿态,她直面自己的“固执”和非舒适区体验,但又总是把自己投入到新的未知的事情里去。她是把自己当作一种方法去实验的,伴随着对不擅长的不确定,一些慌慌张张,然后收获不断变强的承受能力。 这几年,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倪妮都会去尝试,“其实就是在练自己的这种适应能力。”相比电影,电视剧要求演员不断在不同思绪和情感状态间切换,舞台上需要演员与观众构建更强的交流感,专注不懈怠,即便是再演一样的东西,也要让观众能够感受到饱满的表演状态。“都是逼出来的”,倪妮笑道,“我觉得有时候遇到不适应和不舒服的状态反而是对的,太顺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可以,我自己也很舒服,大家也很喜欢,粉丝也很喜欢,导演很喜欢,尤其是作为演员,在被大家喜欢的时候,你可能会听不到实话。” 比起听到各种实话,遭遇进入新事物的不适,倪妮更怕被困在自己的狭隘里——这也是一种她的小固执吧。出演话剧的时候,更有舞台经验的演员和老师会直白告诉她:你这样做不太好,我看不到你在舞台上有主人的感觉,我觉得你是来这看戏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声场传不出去,我觉得你的肢体你在舞台上不够放松……一切当然会让人焦躁。“人还是喜欢听表扬的,我想把这些东西做好,也知道这些问题存在,所以你就得调整自己,就得自己进步,不能要求你的粉丝对你无限宠溺,你所有的缺点人家都不说出来。但走过这个过程后,感觉相当好,比别人什么都不告诉你、无脑夸你要好太多了!”倪妮说。 春风 在短片《春风》的片场,倪妮和朱一龙又相遇了。监视器屏幕里,两位演员和导演在酒吧场景中一直在讨论着什么。在《消失的她》中,倪妮和朱一龙已经磨合好的交流方式继续奏效,他们发问,寻找答案,连接人物的故事线,努力将角色的动机和逻辑理顺,然后放松,把一些空间交给感受本身。倪妮的角色子悠,是拿着一张照片来外婆和她的老地方寻找回忆的。倪妮想,这件事或这个决定在子悠生命中的发生其实是很清淡的。不需要被升华到很高,它是一个心念,犹如春风吹过一般,让人觉得舒服。回到老地方,发现物是人非,引发一些淡淡的情绪——这件事并不刻意,而是会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如果它值得被拿出来讲一讲,不是因为它不寻常,而正是因为它寻常。“你从一个熟悉的地方离开,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然后又从陌生的国家再回来,发现原来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陌生了,就有点像四季更迭一样的感觉,好像每一年的春夏秋冬你都很熟悉,但是每一次更迭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倪妮和朱一龙都很喜欢落地的东西,比如质朴的台词,有烟火气的故事。所以在《春风》短短的篇幅里,倪妮希望能给出一些“清淡”的东西,将情感变得含蓄隐晦,“让观众去摘取他想要的感受,什么改变了,什么留下来了,就让看了这个片子的人们自己去感受吧。” 在《春风》中,子悠对故地的记忆来自于春季的榆钱,倪妮没吃过榆钱,所以请同事们去找,但故事拍摄时季节也几乎过了,所以她对榆钱的认知暂时停留在蒸窝窝头、馒头和植物百科的图片上。但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留给故乡的小角落,倪妮对家乡南京的记忆就被留给了夏季上学路上的梧桐树。那并不是春风般的舒爽,南京的夏天很热,白下区梧桐树的毛毛掉下来落在倪妮身上,被汗固定,她总是动手去挠,然后造成皮肤过敏。但倪妮说,她还是很喜欢那条路边的梧桐树。在对话带来的感觉里,倪妮是个“大女孩”,她眉毛长长的,聊天的时候没有小动作,但会有一些大舒展,比如她会把腿抱上椅子,会利落地拨一拨长发。可以想象她童年的样子:在干休所边的外公外婆家,在农田和池塘边,她在哥哥弟弟的男孩堆里长大,从小被带着爬树,下河抓虫,挖蚯蚓。外公把钓鱼技能传授给倪妮和兄弟们,倪妮就抓蛤蟆钓龙虾,还在土里埋了一个坛子,坛子里养了蛆,蛆臭臭的却是上好饵料。学骑自行车时,倪妮的车没有闸,她从坡上冲下来直接撞在路边平房,磕出来的疤现在还留在鼻子上。倪妮小时候就开始练体育,想去打篮球被驳回,因为教练通过观察认为她长不了那么高;想去练体操也被驳回,因为教练摸了她的骨,说她未来个子会太高。后来,倪妮去练了国标,又练了游泳。说起童年,倪妮没有什么伤感的回想,她说练体育带给了她能吃苦的品质,最重要的是给了她强健的体魄!《春风》中子悠的怅然若失短短出现在倪妮身上,也是在她说起外公外婆家现在样子的时候吧。水泥的很工整的亭子和排水系统取代了兄弟们和她一起走过的农田粪池,挥别孩子们乱糟糟的童年疯狂,那是一座城市一定会去到的地方,却让长大的倪妮对钢筋水泥、高楼大厦、反光玻璃组成的空间无法产生特别的情绪。 “这可能也就导致我特别不爱四处转悠,不爱逛街,比较宅,可能就把自己给锁住了。但其实这样不好,人把自己锁得太死会变得很‘独’,‘独’会让人慢慢变冷漠。所以我也是慢慢觉得要出门,不要这么固执”,她再一次提起自己的“固执”来。聊到这里,我们才发现,一些固执的逐渐松动,好像是这个女生当下一个重要的变化。“你不能老是处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真的得有生活,没有生活连男朋友都找不到!”所以,倪妮现在除了猫咪大乖,还有了一些热情、快乐、活泼的密友。她们会一起在她家整理收拾“断舍离”,也会一起去密室。 在《春风》的结尾,倪妮扮演的子悠看向门外,一阵自然风吹动了酒吧门前的丝带,在拍摄当下,没有人发现有风到访。而这个巧合令导演何一非在剪辑时立刻停止纠结,决定选择这个镜头作为正式结尾。事情就是这样,当锁住的门打开一条缝,春风自然来。
/何一非: 叠加的色彩与回忆/
《春风》的故事与导演何一非的个人经历关联很深,她离开北京去纽约上了快十年学,对故土有着太多回忆与思念,她曾一度觉得自己快要不认识这座城市,因为变化太多太快,而后又重新找到了连结的方法。她将这份细腻的心思变换写进文本,抓住空间里或看见或看不见的新与旧,不断刷上新的色彩。 采访:周禾子

向上滑动阅览
这次和VOGUEfilm的合作是如何开启的? 去年是第一次跟VOGUEfilm合作,我做了《纽扣人生》的执行导演,当时整个片场的氛围和感受都特别好。这一次是通过制片人郑菁,再一次与VOGUEfilm合作。正好《春风》这个故事在我脑海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有一个雏形,所以在有了这次合作的机会之后,我决定好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拍出来。 《春风》探讨归属与变化,新旧交替,留恋与释然,这样的主题是如何确立的? 某种程度上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因为我从2009年到2018年一直在美国读书,将近十年时间,所以有很重的乡愁。我是北京人,总是很想念北京的街道、胡同、老建筑,还有味道。在那段时间里,我每次回来都会对北京变化之快和变化之大有所感触,会有种我终于回来了却不认识这个地方的感觉,甚至我会想有些记忆是不是只存在于我自己的脑海里?是否产生了记忆的错位?这是一个人与故土的羁绊。直到我2018年彻底回国之后,真正地在成年后工作和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我才有一种又与这个地方重新相连的真切的感觉。我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也越来越有感触:我们真正留恋的一个东西或者地方,并不仅仅是其本身,更多地是我们和它以及与它相关的人产生过的过往,物理空间永远都会有变化,有叠加,但这里产生的回忆与感受会一直留下,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叠加与连结。 在确立了朱一龙和倪妮两位主演之后,是否又有对原有的剧本和角色进行调整? 我其实特别感谢两位演员,原先我在写剧本的时候会有比较强的想象,但实际在现场中,有很多地方是我跟他们一起探讨出来的,包括一些台词和走位,比我剧本里的更自然流畅,体会到了和专业的演员共同创作的感觉。但是原来故事里的女孩更加迷茫一些,而我从倪妮的作品和采访里感受到的她是更有力量感、更坚定的,所以我也就在故事里把她的这种女性特质增加了一些。 关于这次《春风》的视觉表达,尤其是酒吧的部分,你是如何去营造出那种新旧叠加融合的感觉?勘景的时候是如何进行考量的? 在勘景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酒吧的选择。我喜欢探索隐匿在大城市中的小店,所以很喜欢去北京胡同里“探店”。我总是觉得,因为生活的地方太大了,在看似平凡的每一个街角、每一个路过的人,可能都在发生着不平凡的事。所以勘景找酒吧的时候,我希望能先有一种藏匿感,然后我希望它能有比较强的堆砌感和叠加感,不是完全现代的,而是有很强的个人特色的。我们现在拍摄的酒吧有原始的木质结构,墙上有很多来自老板的收藏物,有挂在一起的油画和国画,有黑胶唱片也有CD机,这些本就是不同时代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在道具上增加了这种叠加,比如片子里的那个马克杯,我们在它上面贴了眼睛和鼻子,在故事中它们来自不同的客人的“创作”,这是每个人留下的痕迹。 剧情中涉及调酒的部分不少,你是如为何想到借此来推动剧情并引出影片主题的? 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就喜欢去一个躲在日料店后面的清吧喝酒,并在那里观察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脑补创作他们的故事。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人的回忆很多时候都在味觉里,回忆起一个东西的时候总是最先想到它的气味。我之前在一家酒吧尝到过一款以糖葫芦为灵感的山楂做的调酒,我对北京儿时的记忆就是冰糖葫芦,喝这款酒就会勾起我的回忆,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没有吃过冰糖葫芦,他喝了这个酒,也同样获得了属于这个地方的线索,这个脉络是会一直延续的。所以我在《春风》里也把榆钱作为了味道的线索,过去的味道是在面里,现在换成在酒里,只是形式变了,这个空间里过往的回忆会一直在,新的回忆也会产生。 在拍摄完成、做剪辑后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跟在片场不同的发现?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镜头的呈现。 我们的影片叫《春风》,最后一个镜头是想表达这个酒吧在营业的最后一晚恢复了生机,现场我们拍了两条,当时的注意力主要在看演员的表演上。通常情况下我会觉得第二条更好,更符合我的预想,但在真正剪辑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条里,酒吧门帘的彩带真的被一股春风吹起来,轻轻飘动,这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神来一笔,是非常幸运的。 你为何会选择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我最早的启蒙其实是听故事,小学的时候父母会给我买很多磁带,比如有讲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磁带,吃饭睡觉都会听,我也会再去给同学讲故事、编故事;后来我爸爸会买一些电影的光碟回我看,因为爸妈都是大学老师,我一个人在家,也不是生活在胡同那种可以一群小孩一起玩的环境里,就经常一个人看电影,在我孤独和害怕的时候电影给了我很大慰藉。后来我读到一句话特别喜欢,是导演罗伯特·布列松说的——“Make visible what without you might perhaps never have been seen(让人看见没有你就可能永远不会被看到的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我很好奇这一面,我想把这种隐匿的故事讲述出来,去连接不同的人,这大概就是我想做的那种电影。后来我进入了纽约大学的研究生院校,因为李安导演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写了很多他在纽大上学期间的思考和见闻,我非常喜欢他,也想要在这里学习。在这里优秀的人非常多,我在这里尽一切可能最大程度地开发和挖掘自己,有过自我怀疑,但也看到了连自己都不曾见过的自己的其他面。 身为电影行业里的女性创作者,你如何看待女性创作者在当今行业中所处的位置与状态,机会与挑战? 电影行业在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女性故事、女性视角,比以前好很多,但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比如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写一个女孩的故事,这是我作为女孩非常天然的选择,但那个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你的故事主角是女性?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在社会进步了,我也成长了,我开始觉得要更有意识地去表达,过去是“我的视角”,是无意识的,现在想要有意识地去创作只有女性才能讲述的故事。 在你的创作和日常积累中,你是否有尤其关注的女性话题或作品? 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她描写的女性关系非常复杂,有相互支持,也会有嫉妒,而通常我们不愿意这样去看待女性友谊,会规避掉那些灰色的地方,只希望一切都是好的。但女性视角的细腻可以一直挖到很深。我最近在写母女题材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讲述一对母女如何变成为两个女人的关系。因为我小时候觉得妈妈是和爸爸想在一起的,他们是一对,妈妈是被当成家庭结构里的一员去关注的,但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她不只是妈妈,她可以只是一个女人;母亲对女儿也是这样,觉得你是我的女儿,直到有一个契机,她们彼此不再把对方当成某种身份的附属去看待,而是独立的个体,我觉得这是女性视角独有的东西。
/郑菁: 讲述最真实的体验/
继上次的《纽扣人生》之后,制片人郑菁又一次与VOGUEfilm合作,她依然带着满格的动力与真诚帮助导演把故事讲述与传递。这也是郑菁选择制片人这份职业的原因之一:每一次都是崭新的体验,越复杂越令人着迷,无论这其中包含的是困难还是喜悦,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去面对生活,并能以作品来讲述,这是郑菁做电影的愿景与意义。 采访:周禾子

向上滑动阅览
这次与VOGUEfilm的合作是如何开启的? 这是我跟VOGUEfilm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去年的《纽扣人生》。平时我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导演都会有关注、有积累,希望她们能获得一些机会,而VOGUEfilm一直在帮助女性创作者、女性电影人,所以第一次合作之后我跟VOGUEfilm也持续有交流,有好的导演、好的故事我也会推荐。这一次在确定了朱一龙、倪妮两位演员之后,我们觉得何一非导演有个故事挺适合的,她无论是在审美上还是讲故事的方式上都挺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拍《纽扣人生》的时候,一非是那部片子的执行导演,对于拍摄VOGUEfilm的节奏、方式也比较熟悉。所以她对故事做了一些完善和修改,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春风》。 拍摄中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感触颇多的地方? 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很极限的操作(笑),无论是筹备的时间还是实际拍摄的时间,都非常有限,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团队中很多人是参与了上一次拍摄的,所以大家很默契,没有也不需要磨合期,我们会说是“全自动”团队,大家都非常专业,很清楚各自的分工。 你如何看待制片人和导演的关系?以及在一部作品中,制片人的作用和重要性? 我觉得导演和制片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比如在剧本层面,一非对我有非常大的信任,我的反馈她会很清楚如何去做调整,没有质疑。我觉得这减少了很多内损,因为导演和制片人通常会被认为是前者想要在创作上突破,后者则是想要保证能够完成,而我和一非之间就不会有这种争执,很顺畅。我合作过很多年轻的导演,而且越来越年轻,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需求、长短板,我希望我的经验能够尽可能地帮助到他们扬长补短,在交谈与合作的过程中,通过对彼此的了解和判断,一点点建立起信任。完成一部作品,尤其是长片,会有太多的困难,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希望能在各个层面上帮助导演一起推进。 你的履历丰富多变,有着经济系的学习背景,做过电视主持人、编导,后来又选择成为了一名制片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制片人的工作足够复杂,这是我想去挑战的,而且不重复——每一次面对的作品、人、问题都不一样,虽然本质上可能有很多关联或相似的地方,但新鲜感每次都有、都不同。还有一点就是制片人要跟人打交道,我不算外向,也会有自我质疑是否这份工作适合我的时候,但在这个行业里有很多真诚、单纯的创作者们,我总是能遇到跟自己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们,他们让我很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 在这个过程里有没有特别让你难忘的作品或影人? 我觉得每一个我遇到的导演都特别独立、有自己的特点。我最早开始参与的是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导演是澳洲人,叫Sam Voutas,他对中国爱了很多年,他还有中文名,叫司马优,非常喜欢讲中国的故事,那时候他们众筹了一部片,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做,也没钱,但我看了剧本很喜欢,能感受到他们做这件事的单纯,于是我就答应了。这是我作为制片人的第一步;后来的《海上浮城》,预算比独立制作要高,我也遇到了更大的挑战,在前端的创作层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剧本,我也在一点点学,作者向的电影哪些方面需要去坚持、哪些地方需要去保护,而且导演阎羽茜也是女性,这样的合作很好玩也很亲密;再比如2021年《找寻》(Found),它讲述的是在美国被领养和长大的中国女孩寻根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看到这群孩子们的存在;还有中美合拍片《别告诉她》(The Farewell),美方的一些制片人对中国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如何去告诉他们、让他们信任我们中国的团队,也是非常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事情,也很难忘。 就像《找寻》这部作品,你是如何去关注到这样具有女性色彩的议题的?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年龄不同,困惑也会不一样,我很多时候都会去聆听和观察,像《找寻》,就是导演和制片人、正好也是之前拍《别告诉她》里的一位制片人来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因为这是一个跟中国有关的故事,我了解了这个故事和导演的创作初心之后,我觉得能一起去做这件事是很天然的。这些女孩的故事需要被讲述、被看见。 在与国内国外不同的创作团队合作后,你觉得在与女性的生存现状息息相关的题材创作里,中外关注的角度、重点是否有区别? 都会有女性所面对的社会与工作压力、对自我的关注,但是我们国家的女性所面对的情况更复杂一些,比如传统的家庭观念与现代的当下的困惑交融到一起以后,我们如何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做出选择,都很复杂,体现在创作里还是挺不一样的。 你与很多电影行业里的女性创作者合作过,你认为女性创作者最需要得到哪方面的帮助? 很多我喜欢的女性创作经常被说成“不够商业”,这一部分对我来说也是最难的,我希望我能够帮导演们去找到投资,给到最实际的帮助。第一部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第一部拍出来了,接下来才能逐步稳定地去继续创作。能在情感上获得共情的作品一样是有很多观众的,这并不是“商业”的反面,希望大家能这样去看待。 国内女性电影的创作环境近年有着怎样的变化与发展? 你有着怎样的期待、希望能够带去给观众什么样的作品和体验与感受? 创作环境我觉得在越变越好,我希望我带去的作品是能够让你觉得是感同身受的、贴近生活的,无论这种体验是痛苦的还是愉悦的,只要它是真实的,就是我想做的。问题和困境一定都有,但我们必须面对它们,继续生活,尽可能快乐地生活。
平面摄影:黄楚桐 造型:赵慧 Michelle Zhao 编辑:张静 Mia Zhang、周禾子 Hezi Zhou 制作:王珏 Julie Wang 化妆/发型:高建(倪妮)、李鹏坤(朱一龙) 统筹助理:李都 Du Li 时装助理:Alli Chou、Monica Han、Amanda Cao 执行制作:Fatboy Productions 场地提供:兰舍凹飞丝、天黑以后咖啡馆 花絮摄影:Niao N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