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有点边缘,松散得像个很难接到活的艺术家,却在前不久为Gucci拍摄肖战。我们采访了这位略带古怪的摄影师,对他有了些新了解。
冯立的出版物《PIG》
冯立对摄影的态度是,不阐释,不故弄玄虚,“摄影不涉及太复杂的技术,也没什么高深道理,将现实或超现实(hyper-realistic)的跳脱、不可思议捕捉下来就好。照片不需要过分解读。” 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量子纠缠,真实、荒诞,虚无,充斥着失望和惊喜,令人无可奈何。城市市民去公园抱树,中产到海岛颂钵冥想,演绎“eat, pray, love”,巨豪买岛娱乐,尝试极端方式来挑战生命长度——现实就足够戏剧。我们对虚拟屏幕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立体的现实场景,究竟哪个更真实呢?表象下的残酷,以及秩序中的混乱——冯立的照片恰好承载了这种边界模糊的状态,“没人教过我。我只是把自己放到现实中,忙于生存、生活。”作品里原生的粗糙、质朴、野生,打动了视觉经验丰富的创意产业。


2018年,冯立第一次拍摄时尚大片。英国独立杂志《SYSTEM》的团队从英国、美国、日本飞到成都。毕竟冯立彼时还在体制内坐班,“一帮外国人在飞机上紧张得没睡着觉,一是他们全都没来过中国,二是不知道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到底靠不靠谱。”直到冯立按下快门,造型师对冯立说,“你改写了时尚摄影。”当时绝大多数时尚摄影特别板正、商业化,难得看到一个人这么放松、有趣,反时尚的人,把衣服当成道具和装饰来“玩”。这篇很“意外”的中国千禧年专题,由知名作者洪晃撰文,费用是靠给其他杂志拍摄的一组商业片子来支持的。 他的第二次亮相,是在《032c》。看着专门做选角的导演在街道上挑选素人,加上造型、美术、创意、发型、化妆、制片,一群人快闪到一个地方,造一场幻觉,然后立刻消失、还原——冯立被这个工作迷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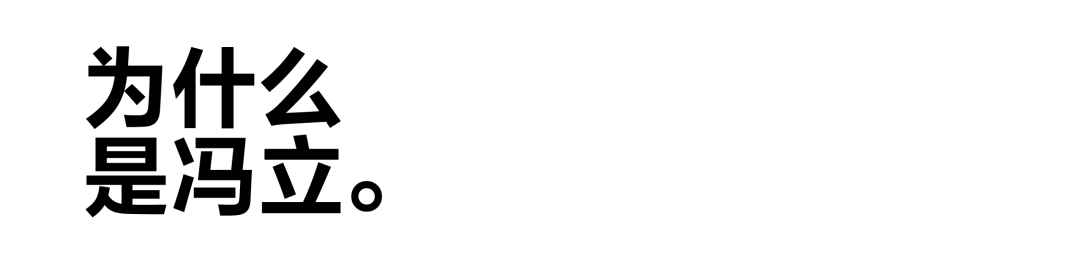
2017年,冯立赢得了第八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新摄影年度评委会大奖”,第三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发现奖。三年前,VOGUE邀请全球22个国家的26名摄影师创作“Creativity创造力”特辑。冯立选择在北京隆福寺的屋顶上拍摄,“现代建筑上有一段假的红墙,前面有假山,很奇异。”鱼竿撑起风筝,在墙面留下阴影,“风筝为什么只能用线来放?为什么不能在水里游?”超模刘雯抱着一条巨型金鱼奔跑,脚下是“伪古典”的中式建筑材料,远处是北京CBD的楼宇轮廓。中国城市的虚实面相,巧妙融合在一张图像。
大片收录于VOGUE U.S.
人们信任冯立的妙想,“有一回,我想把棉花做成粉色的云,漂浮着的,然后牵着它在街上走。杂志团队觉得很浪漫,就帮我去实现这个愿望了。”每个时代都有人做达利,极尽大娱乐家的姿态,调侃自己,冒犯他人,以强视觉冲击跟大众开玩笑,然后被追捧。在2024年的中国,冯立被幸运地选中。 1995年那会,摄影是冯立的爱好,他在政府宣传部专门拍照片,无任何专业训练,甚至揣摩过新闻记者的拍照方式。冯立本身是学中医、针灸的,家里没有艺术氛围。他从小在医院里,看到的都是各式的病人和单调的病床,亲眼目睹病人在眼前去世,心电图拉平,然后被抬走,一个人就这么消失了。 他意识到如果一辈子在这个环境,人会崩溃掉的。“不过进入社会后,发现社会上的人跟医院里的那种状态很相似,有挺多灰色的、亚健康现象存在着,并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体面。”无论是什么国家或阶级,人的复杂性都是一致的。他从不对完美抱有幻想。


冯立的作品,在成都、上海,或其他国家拍的,每张照片的地域特征都不太明显,环境不咋眼,人占了画面的主要位置,闪光灯强化聚焦,不合常理的画面反而会引发共鸣。去年在上海021艺博会的现场,他觉得来看展览的人要比展览本身有趣,所以拍了很多来客的照片,“这些图像,够我再做一个展览了。”
图像的戏剧性在瞬间产生

冯立有种真诚的“玩世不恭”。“是非已经很分明了,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让大家很简化、直接了。我觉得没必要再去强调或评判个人价值观这些。”他尽量隐晦、含蓄地表达。照片是在提问,怀疑现实,然后让人去反思。 有人批判冯立这类街头直觉摄影老生常谈,创作语言鲜明,技术也很直接。的确,竖构图、迫近直闪、硬怼快拍不难模仿,但问题是,拍什么,怎么拍,哪个瞬间、构图,一张图像如何构建剧情?摄影传递的信念是摄影师独有的。“灵感、动机来自于生活,而非刻意的训练。我是个感性的人,能在生活中体会到丰富的情绪,紧张、浪漫、平静的。教育,工作氛围,情感经历等,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形成自己特定的世界观,决定一个人怎样观察周遭世界。”冯立的照片,光鲜、平静之下有种轻快的压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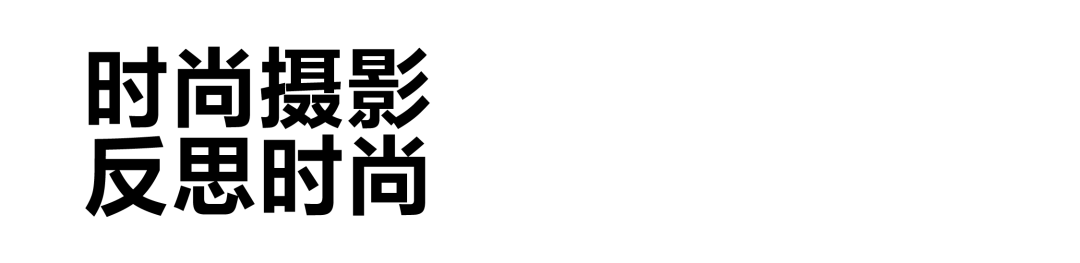
时尚杂志制造幻觉,传播“成为xxx”的幻想。欲望和改变的动力,促进消费行为的产生。 大部分人都不太能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的事实,总想有些异于常人的符号。一定程度上,时尚的奢侈单品,特别是带着打眼标签的产品,比如带logo的包袋、大衣等,是有效的宣言,暗示一种时装审美或生活方式,同时也代表自己属于某个圈层。冯立里里外外穿着优衣库,出入所谓高端场所,“可能因为是一个艺术家,这个身份赋予我一种精英氛围,但如果没有摄影这个tag(保护层),我也会很怯场,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当高高在上的艺术品进入博览会的展台,也仿佛是奢侈品大卖场。即使是美术馆里的塞尚,难道就没有price tag么?只是没明码标出而已。商品化是最佳祛魅手段,“背后的权力逻辑仍然适用。” 尽管明知对所谓高阶层的追求是虚荣所致,但是“没人能例外跳出去,这是种社会机制。”冯立不否认艺术或时尚产业的privilege属性,但也强调,它绝不只关乎金钱与欲望。时尚是当下时代精神的总结,有温情在,“不单是追随大牌。穿着妈妈的衣服,穿着以前爷爷奶奶的衣服,回过头来看,这些单品是很超前的,有趣味的。自己究竟喜不喜欢,穿着自不自在,舒适才重要,别虚伪。”博伊斯喊人人都是艺术家,审美民主化一直在进阶,时尚的话语权从来都是流动的。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美的救赎》里指出,平滑(das Glatte)是当今时代的标签。“它可以将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雕塑品、苹果手机以及巴西热蜡脱毛联系在一起。平滑反映出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平滑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也不会带来任何阻力。它要求的是‘点赞’。”
左为街头拍摄,右为JNBY的商业拍摄

冯立想拍摄真实,而不是“美丽”,“八九十年代的明星每个人都不一样,或胖或瘦,有自己无法被模仿的特点,不用修图。”时尚的责任是引领多元文化,解放审美。卸下矫揉造作、粉饰、光滑的伪装,将现实的丑态、尴尬、不适、窘境呈现。这种看似“反时尚”的举动,却正中时尚评论者下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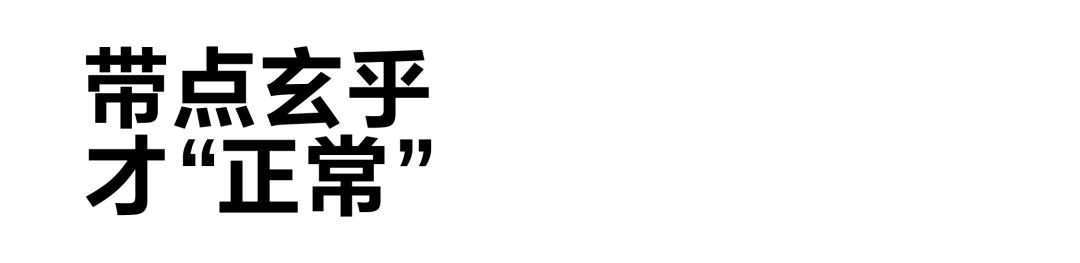
1971年,冯立出生在成都锦江区,读书、学医、体制内工作。2005年,郊外的一场灯会给了冯立很大刺激。 在上千亩的郊外平地上放着节日彩灯,浓雾中,天上什么都没有,巨大的灯箱,像是艺术装置,奇形怪状,有植物、动物、文物,还闪烁着不同的光。冯立回忆,其实灯会在城市区域也有,人们只觉得它像是游乐场,是热闹的娱乐产物。但将它置于荒郊野地,这些灯光装置就发生了质变——司空见惯的东西被重置,仿佛电影一样。 “我那会儿觉得太xx当代了!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当代,或者什么叫艺术。只是突然间觉得,这个世界跟我之前看到的,理解的不一样了。仿佛突然进入了科幻片,对我来说,就像一场白夜开始。”

冯立作品里很多画面就像AI制作的一样虚幻,但又确实是他在街头拍到的。“那种几个人滑着滑翔伞从马路上一晃而过,我甚至可以跳起来把它给拽下来。在成都春熙路上车水马龙的地方,会有这么超现实的事情发生,简直不可思议,这种虚妄的图像信息不断叠加,刺激着我。” 老天眷顾冯立,给他安排了很多奇妙的事。 大概在2008年于伦敦旅行时,冯立去过一个鹦鹉园,当时就许下愿望期待自己能有一只鹦鹉,“一年前,突然有一天,有只鸟就出现在我的窗户前,看着我。我一直养着这只鹦鹉。”


之后机缘巧合,冯立捡到了一头猪,养到现在,也已经八年,“爷爷在几十年前,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在国营的肉联厂里面杀猪,每天在流水线上杀猪、杀猪,再把猪肉提供给菜市场。我倒没觉得说应不应该,但是我觉得看到那头猪的时候,好像觉得是在还债,它来找你了,跟你有关系。” 冯立养了它之后,还真就特别顺利,或许是种善意的偶然。“在跟杂志、品牌合作时,有的会拿着我拍过的照片做参考,但我会说,这东西没办法复制,哪怕制同样的景也没用。”不期而遇,未经审视的意外,才是spark所在。 “北外滩有一大片的金色麦田,人站在麦田里可以看到整个东方明珠塔,我当时就在想,得多高的预算,多厉害的美术老师才能制出这样的景呢?又怎会想到一个,粗糙得恰好的画面呢?”冯立觉得,艺术作品要是太执着于完美,反而让人一点都相信不起来,瑕疵会打动人, “我不相信艺术,但是我不得不感叹生活。”


前一阵,冯立在网络上看到一条“上海陆家嘴苏州拿地被套7年,起诉索赔100亿元,法院已立案”的新闻,花85亿元买地,之后发现买到的是污染严重的“废地”。表面上建构起的美好,没有根基,随时都可以被推倒。“所以,不管是时尚艺术,社会研究或是政治话题也好,一切问题只有回到哲学层面上,才会迎刃而解。都是玄学,或许有神秘力量吧。不像是西医化验血常规这种,都有出处,是理性的。我本身学中医,神农尝百草,理论体系都是抽象、感性的。用虚幻去应对虚幻。” 冯立不是犬儒或虚无主义者,他依然常被具体生活里的美好触动。他看似没太社会化,但其实喜欢人群密集的感觉,“我觉得我是个旁观者,不属于他们。就像我的作品可以在任何哪个圈子里出现,但总是处在边缘。但你真把我扔到一个无人区,我受不了。我喜欢看到人,喜欢嘈杂。”冷漠且爱热闹,典型的现代式割裂。“Fotografiska这个艺术场馆开幕的头一天,执行人员还在忙乱中,大老板从柏林飞过来,想提前跟大家见个面,喝杯酒,加把劲。结果,他把所有的保洁阿姨、工人、师傅、保安全部请到了酒会现场。”


冯立参加过很多开幕活动,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这些不“fancy”的人请到酒会里。保洁阿姨端起香槟,一开始还有点羞涩、局促,后来也逐渐放松,干杯,喝了起来。不管这个看似人道主义的举动是不是套路,总强于无作为。“那一刻,没人关注艺术,但又特别‘艺术’。”如今的时尚从业者,试图捕捉“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

撰文&编辑:马儒雅Maya 设计:晓霓 图片由冯立、Fotografiska提供









